年轻华人清明祭祖,传统礼数在澳延续!“每年总得有一刻,是留给故人的”(组图)
清明时节,是华人“欲断魂”的时刻。部分身处澳洲的他们,也选择以传统礼数祭拜祖先。
不少年轻人在遵循着传统,他们去到庙宇或墓地烧“元宝”,双膝跪地;也有人在家象征性烧点纸钱,寄托哀思。
“这样做,心里会好受一点。”他们说,“要是想到了不做,心里会过意不去。”
这仿若移民生活中,一页再普通不过的“日记”。“写”好合拢后,第二日又再如常走入澳洲布满哥特风格建筑的街头。
“宁可信其有,希望他们在‘那边’过得好”
4月2日 早9点半
27岁的Emma抵达悉尼圣关帝庙。往年都是与家人一起祭奠爷爷奶奶的,今年无法回国的她,只好找了庙宇。
因是工作日,人不算多,她迅速向工作人员咨询祭拜流程:先拜神仙、再烧元宝。元宝分两种,她挑了最贵的。往常在中国祭奠时还会准备供品,在澳洲,这已是她能做到最力所能及的“豪华”了。
跪拜完一众神仙,她拿着“大元宝”到专事焚烧的露天地点,在油灯上点燃元宝,送进炉子,一边跪倒一边口中念念有词,一套动作多年来早已熟稔。
“我说让爷爷奶奶来收钱了,这是给他们的海外‘汇款’,”她说。
正在这时,旁边另一位同来烧钱的中年华人大姐对她说,“你看,风突然变大了,一定是家人收到了。”
“一下子觉得心里很安慰。”做完一切,她起身拍拍膝上的土。

圣关帝庙里烧纸钱(图片来源:供图)
Emma来澳洲已7年,爷爷在2023年去世。她从小是爷爷带大,情深意切。即便不能回国上坟,也一定要在澳洲完成这个仪式。
“我在爷爷身边长大的,深刻的记忆太多了。”她说,忘不了小学时爷爷每天接送;读大学坐飞机前,爷爷一直目送离开;每次出去玩,爷爷总给她塞钱;自己舍不得花钱,但是会陪她这个孙女去逛街。
Emma说:“最后在病床上,那么难受了,也只有我能和他沟通。”
她虽然是年轻人,却并不觉得这样的仪式是“封建迷信”。
“没有亲人走,你可能会觉得是封建迷信,但如果是你的亲人,你真的会宁可信其有,希望他们在‘那边’过得很好。”

圣关帝庙(图片来源:供图)
Emma也曾想过“在澳学澳”,以西人方式鲜花点烛祭拜,因最终放弃了。“爷爷的碑坟都不在这,去哪里献花?我觉得不靠谱,花不能吃也不能喝,爷爷奶奶在泉下也不希望那样。”
对于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的看法,她表示,他们都信“玄学”,“主要是这样我的心里会好受一点。要是想不到就算了,要是想到了不做,心里就会过意不去。”
对于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“代烧”广告,她则不看好。“我觉得挺傻挺离谱的,这种事本来就是心意比较重要。”
“每年总得有一刻,是留给故人的”
4月3日 晚7点
30岁的Liz一家在自家院中祭祖,作为清明节的传统,父母和她已坚持9年。
在中国老家,亲人们都去上坟祭奠。这个家庭即便跨越了千山万水,还是深深惦记故去的祖辈,依然坚持维持这个小小的仪式。
全家移民澳洲十几年了,虽已融入西人社会,但唯有面对祭祖这一关就是不行。对他们来说,元宝和纸钱才是“对”的。
Liz说,“这不是迷信,只要你的母语是中文,‘烧钱’、上坟这个传统就是认得人的根脚。每年总得有一刻,是留给祖辈的。”
没有香案、没有祭品,一缕青烟,一点心意。简易的铁皮灶是奶奶生前来澳洲时亲手所制,一直沿用至今。那是奶奶留下为数不多的念想,似乎成为一家人情感上的归处。


(图片来源:供图)
澳洲对明火管理极严,任何一点烟气都可能招来邻里投诉,甚至触法。于是,为了不违规定,也为了不惊扰四邻,他们每年只敢准备极少的纸钱和元宝。小心翼翼地点燃,一缕青烟刚起,就又急急扑灭。
只求心意,不敢铺张。
今年,全家人亲手折了几十个锡箔“元宝”,还买了一沓纸钱,是澳币,想必奶奶在下面不会“手紧”了。
“奶奶就是奶奶啊,烧纸的时候就会想起她,有时想起她烧的菜。”
Liz说,自小在奶奶身边长大,她最喜欢奶奶做的腌西瓜皮和醉蟹,只是最后那一次,奶奶挣扎着为她做好,一尝,却咸得发苦。“老人家味觉不太灵了,还是坚持给我做了一次,结果放料放太多。”
“我没吃多少,奶奶会伤心吧,”她至今耿耿于怀。

(图片来源:供图)
这些点滴都是她在烧纸时浮现在脑海的,“我们不会流泪,但会轻声和已故长辈说说话,告诉他们家里一切都好,请他们放心。”
她说,会把这一传统传承给自己的宝宝,“会按我自己的理解跟家里的小朋友解释,总之就是给长辈的礼物。”
胡兰成说:“人要有敬,不然活着也是空的。祭祖不是封建,是知道自己从哪里来,要往哪里去。”
Liz觉得,知道从哪里来很重要,那是“无力抗拒”、“身不由己”。
“烧的是对先人的思念和关心”
4月4日 午12点50分
25岁的中国留学生Eaden前往Macquarie Park的墓园祭奠爷爷,原本只有亲友葬此才能来祭拜,但他说明情况后,终网开一面。
这里有一个区域里华人长眠者居多,因此专门准备了烧祭品用的铁皮桶子。
也实在是无奈之举,因为住公寓,对明火的管理很严格,他不得不寻找一个妥善可烧火的地点。
“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烧会比较合适。公寓里比较难办,我怕会被投诉;本来找好的了一个庙,算好的那个时辰又不开门。”
之所以今年如此隆重,是因为爷爷在国内“迁坟”,这是习俗中一件大事。父母希望他也能在澳洲有些表示,他为此专门采购了祭品。纸别墅、纸豪车,甚至有白切鸡和龙虾。
墓园里,他依次将这些纸扎物件丢进桶里,点起火焰。所有对长辈的思念都化作一缕青烟,放佛飘向不知哪里的彼岸。

Eaden在墓园里的小祭台(图片来源:供图)
Eaden自小没了爷爷,对爷爷本没有什么印象,但在广东习俗里,清明祭祖是一件大事。因为祖上三代都制香,每年清明的上坟仪式全家都会大摆“阵仗”。从小时候的“看热闹”到长大后的亲自参与,他没觉得这“风景”是隔了一层的。
他每年都亲眼看到丰富的供品,纸扎房子、金银财宝,iPhone、iPad不一而足。广东人家每年还会准备很多食物,乳猪、白肉、鸭蛋、水果、白酒等。
因此,他对这种事觉得正常而安然。来澳5年的他,毕业后干脆在悉尼一个殡葬家族从事相关工作。
今年清明的祭奠,他准备了很久,身在澳洲还是尽力而为地回归传统。他一边烧着祭品,一边煞有介事的念念有词。
“我都是跟我奶奶学的,要说是烧给谁的,”他说:“然后我说‘爷爷,我给你烧了大房子住,大车子开,还烧了龙虾给你吃,希望你可以好好享用,保佑我’。”
求祖先保佑子孙,是祭奠必不可少的“规定动作”。

买了豪华祭品给已故爷爷的Eaden(图片来源:供图)
祭品算豪华,唯一缺少的是在中国祭奠时的人情味。“我记得在国内上香烧纸前,家人会趁这个机会与许久未见的成员聊天。”
这和《今生今世》里描写的一样:“清明的时候,一家子带着饭菜酒水上山去祭祖。扫墓的时候大人烧纸,小孩子就在旁边放风筝,或者追着蝴蝶跑。纸钱烧成灰,风一吹就卷到山谷里去,像是给祖先送去了信。男人磕头时是实实在在地磕,女人和孩子就点点头而已。”
又说:“祭祖不是伤感的事,反而是热闹的,像是一次家族的小型团聚,有人说话,有人低头哭,还有人笑着讲去年谁家添了孙子。死者已经不在了,可人活着还是要同他们说话。”
Eaden说,“小时候我会觉得,烧这么多纸钱,到底先人们什么时候才能花完。长大后才懂,烧的是我们对先人的思念和关心。”
“我不觉得这和年龄或在哪里有关系,我觉得是对祖辈的纪念。”
他说:“能跟国内的家人在不同国家用相同的方式祭拜祖先,对于我来说,更像是一种情感的连接。”
(记者 艾欧)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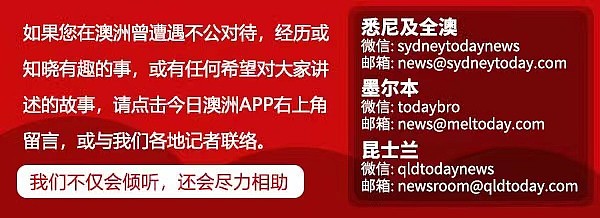




 +61
+61 +86
+86 +886
+886 +852
+852 +853
+853 +64
+64


